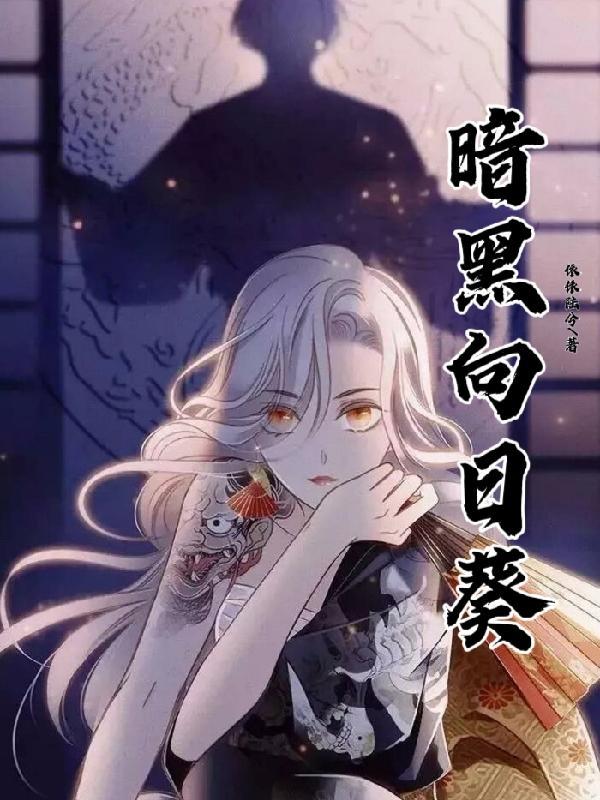冰雪小说>一个太监的暗恋史 > 分卷阅读11(第1页)
分卷阅读11(第1页)
后少花心思。咱家还有当值,姑娘自便吧”
人已掀开帘子走远了,宋长瑛才收起脸上些许的娇态。
太后睡得不稳当,夜里又惊醒。裴端跪在扶她坐起身,只看她混浊的眼里露出些悲意“皇上呢什么时候走的”
“太后娘娘,皇上是守到子时,才回去歇息的。”
太后又剧烈咳嗽起来,裴端忙拿着帕子接,手心又染了温热的血色。
伺候太后喝了热水,她方才歇下。裴端不动声色地打量她满脸病容,知道太后已经时日不多,上一世就是在年后不到半月,就薨了。
太后母家并不如何显赫,皇上甚至都不是她亲自抚养,初登基那几年,原是皇帝养母永仁坐的太后之位。当今皇后娘娘也就是先太后母家,外戚势大时,太后没少受过刁难,如今却没享受几年好福,就病体沉疴,无力回天了。
太后一死,皇帝心里愧疚更甚,对皇后及其亲族更为忌惮,又看着日益挺拔的太子,猜忌之心渐渐升起,连连借着宦官之手削弱太子党羽,最后逼得父子反目,太子造反。连带着站错队的裴端也险些掉了脑袋,若不是皇上对他颇为宠信,恐怕早就在太子谋反时掉了脑袋。
就连宋长瑛父亲宋贺,虽然裴端没有明确证据,但后来也察觉恐怕是因为与太子一党牵连,才遭此横祸。
本来也不算不上定局,里头还少不了贵妃挑拨,裴端若是想,以皇上后来对他的信赖,父子之间不说化解矛盾,但肯定不会闹到必死局面的。只是裴端扪心自问,并不再想偏帮太子。
一是上辈子太子舍弃自己在先,裴端天生心眼极小,记仇得很。
二来,宋家一案让裴端对太子性子很是忌惮。宋贺虽然不算清正廉洁的好官,倒也是个能臣,皇帝原先是有几分看中他的。之所以获罪如此之快,除了贵妃一脉暗中作梗,估摸也是太子主动割肉保全自己的手段。
天家之人,没有不多疑的。他既然用宋贺,手里必然也拿着宋贺的把柄,
也仅是他们这些宦官,既不被看得起,也不会被当做威胁。
三来,比起两位成年且皆有后台的皇子,年幼的五殿下显然更听话些。
太后呼吸声渐渐平稳,裴端这才轻声慢步地退下,阖上门走了出去。
丑时,换班的太监已经赶来,裴端交了差,嘱他们静心伺候,才回到耳房。
一推门,就见那穿着青釉色的宫女服的身影仍然在里头,一手撑着脸颊,垂着头正打瞌睡。
裴端步履轻巧地走进屋里,伺候人惯了,硬是没有半点声音,没惊醒宋长瑛。
耳房的茶水还在暖炉上咕嘟嘟的热着,地上打翻的糕点已经被收拾干净了,桌上又多出新的食盒来,点心热汤都在小碗里盛着,散出香味。
他情不自禁地靠近那正打盹的少女,心里一块蠢蠢欲动,忽然好像又是前世自己成了孤魂野鬼的时候。
外头下着雪,天气很冷,屋里火炉却烧的暖烘烘的,周遭也没有旁人,安静极了。宋长瑛坐在桌前翻书,他就仗着无人瞧见自己,伸手带着恶意地去拧了对方的脸颊。
“”真是鬼迷心窍
几乎要真的碰上宋长瑛的脸时,他才猛地回神,狠狠地敲了桌子,在宋长瑛尚带困意时阴笑道“姑娘见了那情形倒也敢在咱家这睡,小心叫人拖去角落里投井。”
“瑛娘失礼。”宋长瑛推了推食盒“先前的洒了,长安说您这几日忙,晚上也没吃饭,钟粹宫的小厨房还算可以,公公将就吃些吧。”
收拢在袖中的指尖将掌心掐得泛白,裴端挺直了脊背,刻意掩盖什么似的,语调平平道“姑娘既然知道咱家这忙,就不该多来添事端,司礼监多的是有人给咱家送吃食,不劳姑娘烦心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