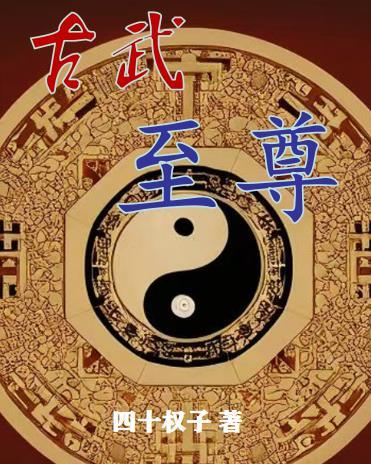冰雪小说>大小姐在种地综艺里爆火出圈 > 第184章 收粮(第2页)
第184章 收粮(第2页)
楚旸反复不停地喝水,反复不停地上厕所,如此循环往复。
虞向晚不知从哪儿找来的钩针毛线,坐在沙上就开始针织围巾,她不断地钩错不断地拆线重织,大半天下来也没见她钩出什么花样。
另外三个大男人围坐在茶几边上喝茶,从早上喝到下午,总共也就喝了三壶茶。
最后还是姜禾禧沉不住气,从椅子上霍然站了起来。
“我实在是熬不下去了,要去研究中心的门口去等结果,你们谁和我一起?”
“姐,我跟你走。”
楚旸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响应她的人。
俩人匆匆忙地往外走,等到动面包车准备开出去时,剩下的四个人前后脚地走了过来,拉开车门,一个个地全挤到了车上坐着。
姜禾禧鄙夷地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们一眼,动车子,在秋风瑟瑟里,驶向了去往市里的路上。
一行人抵达研究中心后,化验结果还没有出来。
他们各自坐在实验室门口的长椅上。
每当有穿白衣服的研究人员从面前走过时,他们齐刷刷地抬头,目光一致地从人家的身上扫过,直到那人远去后,才统一地收回目光,继续等待。
如此浩大的声势,逼得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优先化验了他们的高粱,争取第一时间得到检验结果,给他们一个交代。
姜禾禧的忐忑不安,只有在听到沈应禹一遍遍地核算高粱的收益时,才能得到稍稍的缓解。
“大禹,你再算一遍收益,我想听。”
沈应禹不厌其烦地说道:
“我们种了六百亩高粱,按照平均亩产六百斤来算的话,现在酒厂给到的平均价格是两块一毛五,合起来是多少?”
“我懒得算,你直说。”
“七十七万四千。”
这个数字足以安慰到在场的每一个种地人。
姜禾禧坐在长椅上,双手合十地抵着额头,虔诚地做起了祷告。
实验室的门被人推开,“吱呀——”一声响,她条件反射地站了起来。
“出……出来了吗?”
“项目名叫财阀五人组的高粱地的结果出来了。”
研究人员拿着新鲜出炉的化验报告单,见长椅上坐着的人个个挺直了腰背,目光炯炯地朝他看了过来,顿时感到了压力山大。
“你们想听最好的那一份化验结果,还是最坏的?”
颜阶稳稳地出声道:“最坏的结果。”
研究人员翻出第二张单子,宣读道:
“o2号样品抽检结果:红缨子高粱色泽气味外形合格,高粱水分15。1%,糯性97。3%,不完善率o。7%,杂质的标准率o。87%,符合酒厂的收粮标准,恭喜你们。”
楚旸惊呼一声,从长椅上跳了起来,意识到失态后,他牢牢地捂住了嘴巴,一头扑到了沈应禹的怀里。
虞向晚靠在墙上,止不住地笑个不停。
只有姜禾禧安安静静地站在过道上,一动也不动。
颜阶看到她的手死死地攒在一起,他走到她身后,抬手抚了抚她的短,安慰出声:
“好了,别哭了。”
她低了头,两行滚烫的泪水随即砸落在了地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