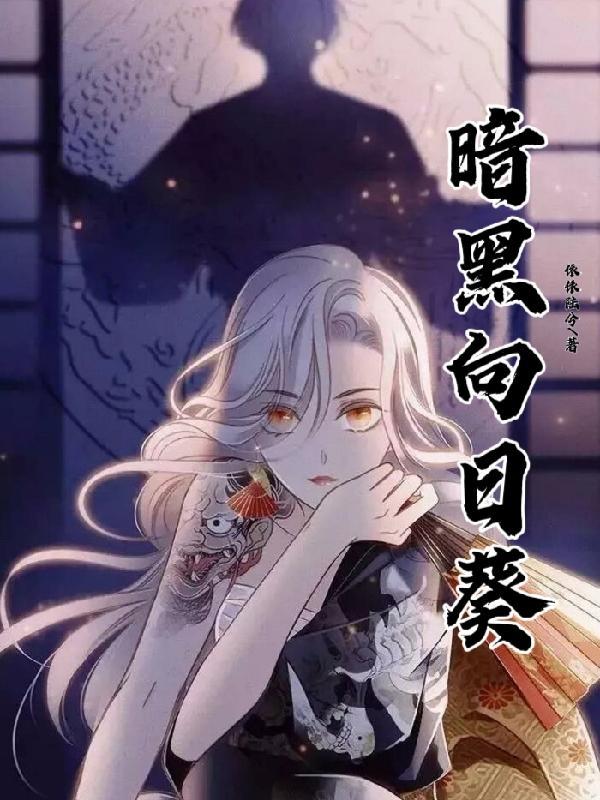冰雪小说>卿为佳人 > 第35章(第1页)
第35章(第1页)
可他候了半晌,待到沈余欢收拾好碗筷去前厅准备坐诊了,也不曾听到后面那半句话。
林梦寒清澈的眼神晦暗不明,胸腔酸涩难耐,恨意丛生,肆意蔓延,只想抓住重远道狠狠收拾一顿才能解气。
怎的重远道一来待遇就这样好,吃喝住一样不缺,如今还白白捡了她的关怀去,倒是他,从泼水开始就显得里外不是人。
但想着一头是心悦之人,另一头是分别数年重逢的兄弟,他终究还是咬咬牙忍下了。
罢了,说到底也是他自作自受,总归他从头到尾也没对沈余欢有过任何明确的示意,胆小退缩的是他,暗暗吃味发疯的也是他。
沈余欢秀外慧中,任何男子与她接近都会被她所吸引,他没道理仇恨重远道,只恨自己明明近水楼台,不仅没先得月,反倒可能还让旁人捷足先登了去。
重远道若是执意与他争,倒也无妨,最关键的是沈余欢如何想,所谓强扭的瓜不甜,她若是不喜悦,那重远道花再多心思也终是于事无补。
可她到底如何想的?明明同他相遇后很长时间里都计算地分明,为何如今轮到重远道,倒是少了那许多的试探和泾渭分明的界限……
他若有所思地看向沈余欢,后者端坐在案边,青葱柔白的手指伸出,为问诊的病人探脉。
眉头微锁,神思凝注,片刻后,收回搭脉的手,执笔在宣纸上书写,行云流水,仿若那些病症和药方是她牙牙学语时便刻印在脑海中,伴随她二十余年,用时就像幼童叫出的第一句“娘亲”般,水到渠成。
好像不管认识多久,她就坐在不远处,无需多言,一个动作便能轻易挑动他的心;
就像初见时那惊鸿一瞥,他泥足深陷,至今不能自拔。
那感觉就像坠入沼泽地,初陷进去时,觉得无伤大雅,一旦你开始挣扎,它便会像一张巨大的网,从四面八方将你团住,漩涡一般吸住。
你别无他法,只有臣服。
重远道算什么,他自不会将沈余欢拱手让人,和平竞争不可耻,只要能换得她垂怜,刀山火海,他闯过去就是了。
这边林梦寒做了冗长的心理建设,那边重远道却笑得喜不自胜。
老四见证了方才桌上的一整套,如今看重远道只觉得他不识抬举。
医馆众人早已瞧出林二东家对沈东家有意,他身为林二东家的兄弟,难道瞧不出?
他转头看向老三,故意大声道,“老三,你说一个大男人喜欢装柔弱是什么病?”
“什么病?”老三没反应过来,问道,后添了句,“你要看病的话得找沈东家,我可不懂这些?”
末了,又添了句,“我说四弟,二位东家待我们是真好,你可别做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事!”
说着,上下打量老四,出口颇为语重心长,“装什么柔弱?就你那身板,你柔弱什么啊?一百斤的大米你一次扛三袋,别到了君康堂,看二位东家待你好,你就肆无忌惮,得寸进尺……”